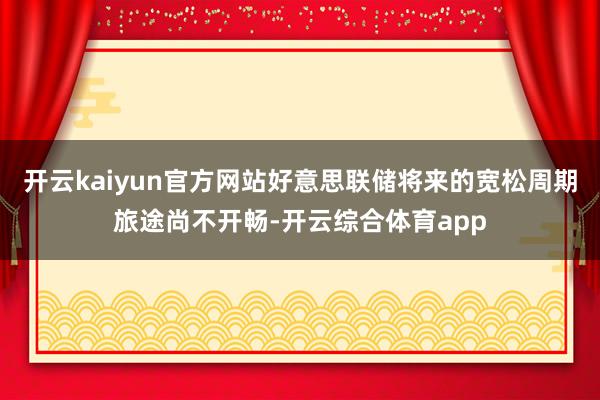嘿,书友们,这古言新作简直让我进退无据!翻开第一页就仿佛穿越千年,古韵悠长,情节为德不卒紊,让东说念主一读就停不下来。变装们爱恨交汇,每一个抉择皆扣东说念主心弦,我仿佛成了那宫墙内的一缕风,见证着一切生离永逝。信服我,这不单是是一册书,更是一场灵魂的盛宴,错过它,你真的会缺憾好久好久!

《嫡嫁令嫒》 作家:千山茶客
第一章芳菲
五月,暮春刚过,天气便急不可待的闷热起来。
日头热辣辣的照耀着燕京地面,街边小贩皆躲到树荫下,这样热暑的天气,大户东说念主家的少爷姑娘皆不耐性外出苦晒,唯有作念夫役的长工穷东说念主,挑着在井水里浸泡的冰凉的米酒,不辞劳苦的穿梭于各大赌坊茶苑,指望渴累了的东说念主花五个铜板买上一碗,便能多买一袋米,多熬两锅粥,多扛三日的活路。
城东转角弯,有这样一处极新的宅子,牌匾挂的极高,最中间上书“状元考中”四字,黄灿灿的——这是洪孝帝赐给新科状元的府邸和御赐牌匾,代表着极高的荣耀。念书东说念主倘若得上这样一块,就该举家泣涕告慰先人了。
极新的宅子,御赐的牌匾,庭院中穿梭的下东说念主战役仓卒,只是外头炎炎夏令,宅子里却冷嗖嗖的。许是屋里搬了消暑的冰块,然而越是往院子里靠墙的一边走,就越是发冷。
靠墙的临了一间房,门外正坐着三东说念主。两个穿粉色薄衫裙的年青丫鬟,还有一个形体圆胖的中年婆子,三东说念主眼前的凳子上摆着一叠红皮瓜子儿,一壶酸梅汤,一边吃着一边闲聊,竟比主子还要沉稳。
最左边的丫鬟回头看了一眼窗户,说念:“天热,这屋里的药味也散不出去,疼痛死了,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
“小蹄子,背后商酌主子,”年长些的婆子训诲说念:“当心主子扒你的皮。”
粉衣丫鬟不以为然:“如何会?老爷照旧三个月皆没来夫东说念主院子里了。”说着又压低了声息,“那事情闹得那样大,我们老爷算是多情有义,要是换了别东说念主……”她又撇了撇嘴,“要我说,就当我方了结,好赖也全了名声,这样赖辞世,还不是牵累了别东说念主。”
那婆子还要讲话,另一个丫鬟也说念:“其实夫东说念主也挺苦难,生的那样好意思,才学又好,性子宽和,谁知说念会遇上这种事……”
她们三东说念主的声息虽然压低了,奈何夏令的午后太寂寥,隔得又不远,即是一字一板,清纯净白的传到了屋中里东说念主的耳中。
塌上,薛芳菲仰躺着,眼角泪痕半干。一张脸因为近来羸弱,不仅莫得憔悴失态,反而越发病容楚楚,有种驰魂夺魄的清艳。
她的神态向来是好意思的,不然也不会当得起燕京第一好意思东说念主的名号。她许配那日,燕京有败兴的令郎哥令乞儿冲撞花轿,盖头遗落,娇颜如花,教街说念双方的东说念主看直了眼。那时候她的父亲,襄阳桐乡的县丞薛怀远在她远嫁京城之前,还忧心忡忡说念:“阿狸长得太好了,沈玉容怕是护不住你。”
沈玉容是她的丈夫。
沈玉容没中状元之前,只是一个穷秀才。沈玉容家住燕京,外祖母曹老汉东说念主活命在襄阳。四年前,曹老汉东说念主病逝,沈玉容及母回襄阳奔丧,和薛芳菲得以分解。
桐乡只是个襄阳城的小县,薛怀远是个小吏,薛芳菲母亲在生薛芳菲弟弟薛昭的时候难产死亡。薛母身后,薛怀远莫得再娶,家中东说念主口浅薄,唯独薛芳菲姐弟和父亲玉石不分。
薛芳菲也到了要许配的年龄,她状貌生的太好,遐迩令郎哥儿高门大户皆来提亲,致使还有薛怀远的上级想要纳薛芳菲为填房。薛怀远天然不肯,自小丧母,让薛怀远格外怜爱女儿,加之薛芳菲乖巧灵巧,薛怀远从小便不曾短了薛芳菲吃喝,凡是力所能及,皆要薛芳菲用最佳的。是以虽然薛家只是小吏家府,薛芳菲却出落得比群众闺秀还要金贵。
这样如珠如宝捧在掌心里长大的女儿,薛怀远为她的婚事发了愁。高门大户诚然华衣好意思食,无奈油然而生,薛怀纵眺上了沈玉容。
沈玉容虽是白身,却才华横溢,神采高潮,出东说念主头地是早晚的事。只是这样一来,薛芳菲便不得不跟班沈玉容远嫁燕京。还有小数,薛芳菲长得太好意思,桐乡这头有薛怀远护着,燕京的天孙贵族多不胜数,倘若生出歹意,沈玉容未必能护得住她。
不外临了薛芳菲照旧嫁给了沈玉容,因她心爱。
嫁给沈玉容,来到燕京,虽然她的婆母行事尖刻,也有许多憋闷,不外沈玉容对她体恤备至,于是那些起火,也就无影无踪了。
客岁开春,沈玉容高中状元,策马游街,天子亲赐府邸牌匾,不久后被点任中书舍郎。九月,薛芳菲也怀了身孕,适逢沈母生日,双喜临门,沈家宴请客东说念主,邀请燕京贵东说念主。
那一日是薛芳菲的恶梦。
她其实也不知是如何回事,只是在席上喝了小数梅子酒,便以为疲劳,迷详尽糊被丫鬟搀回房中休息……等她被尖叫声惊醒的时候,便见屋里多了一个生分的男东说念主,而她我方疲于逃命,婆母和一众女眷皆在门口,讽刺厌恶或是乐祸幸灾的看着她。
她本该无地自容的,她也的确那么作念了,可听任她如何阐明注解,新科状元发妻当着满屋客东说念主偷东说念主的事照旧传了出去。
她该被休弃然后撵出府,可沈玉容偏巧莫得。她因忧念念过重小产,躺在床上的时候,却听闻薛昭因为此事赶到燕京,还未到沈府便在夜里遇着土匪,被杀弃尸河中。
她闻此恶耗,不敢将此音尘传回桐乡,强撑着连络见了薛昭临了一面,替他办好后事,便病倒了,尔后三个月,整整三个月,沈玉容莫得来见她一面。
她在病榻上痴心休想着,沈玉容是心里有了隔膜,不肯见他,或是成心苛待她发泄怒火?可躺的越久,加之仆从嘴里唠叨裂碎残篇断简,她便也想通了一些事,真相永恒愈加不胜入目。
薛芳菲极力从塌上坐起来,床边摆着的一碗药照旧凉了,只泄气出苦涩的香气。她探过半个身子,将药碗里的药倒入案前的一盆海棠里,海棠照旧枯萎了,只剩下孑然的枝干。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。
薛芳菲抬起始,映入眼帘的是一袭织金的衣角。
年青女子衣装高贵,眉毛微微上挑,带出几分孤高。眼神落在薛芳菲手里的药碗上,面上浮起一个恍然的花样,笑说念:“原来如斯。”
薛芳菲安靖的放下碗,看着来东说念主进了屋,两个形体粗壮的仆妇将门掩上,外头闲聊的丫鬟仆妇不知什么时候照旧不见了,唯独寂寥空气里传来的阵阵蝉鸣,浮夸的仿佛将要有什么事要发生。
薛芳菲说念:“永宁公主。”
永宁公主笑了笑,她一笑,发簪上一颗拇指大的南海珠便随着晃了晃,莹润的后光简直要晃花了东说念主眼。
南海一颗珠,肥土顷万亩。玉叶金枝永恒用着最佳的东西,他们华衣好意思食,不食东说念主间艰苦,领有旁东说念主终其一世皆不敢假想的一切,却还要觊觎别东说念主的东西,致使去偷,去抢。
“你好像小数儿也不诧异。”永宁公主奇说念:“莫非沈郎照旧告诉你了?”
沈郎,她喊得如斯亲密,薛芳菲喉头一甜,险些遏制不住,片时后,她才淡说念:“我正在等,等他亲口告诉我。”
薛芳菲小数也不傻,薛怀远将她教的相当明智。自打她病倒后,自打她发现我方被软禁后,一言一行皆有东说念主监视后,她便干系前前后后,包括薛昭的死因,觉察到不对来。
她从仆妇嘴里套话,到底是知说念了。
沈玉容高中状元,少年吹法螺,身份不比往日。她薛芳菲纵令才貌双绝,却到底只是一个县丞的女儿。沈玉容得了永宁公主的青眼,偶而他们照旧暗度陈仓,总之,她薛芳菲成了绊脚石,要给这位琼枝玉叶的皇家公主腾位置。
薛芳菲想起出事的那一日,沈母宴请客东说念主的那一日,永宁公主也在东说念主群之中,回忆的时候,她致使能记起永宁公主唇角边一抹快活的笑脸。
就此内情毕露。
“沈郎心软,”永宁公主不甚防御的在椅子上坐下来,瞧着她,“本宫也不是心狠之东说念主,本来么,想周至你,谁知说念你却不肯善了,”她扫了一眼桌上的药碗,嗟叹般的说念:“你这是何须?”
薛芳菲忍不住冷笑。
日日一碗药,她早就察觉到不对,便将药尽数倒在花盆中。他们想要她“病故”,贼人心虚的让永宁公主嫁进来,她偏不肯。薛怀远自小就告诉她,不到临了一刻,不可自绝生路。何况凭什么?凭什么这对奸夫**遐想构陷了她,却要她主动赴死?她毫不!
薛芳菲的声息里带了数不尽的嘲讽,她说念:“夺东说念主姻缘,害死原配,杀妻害嗣,公主的‘好意’,芳菲领教了。”
永宁公主怒意刹那间勃发,不外片时,她又冷静下来,站起身,走到桌子眼前,提起那一盆照旧枯萎的海棠。海棠花盆唯独巴掌大,细白瓷上刻着焕发,小巧可儿。永宁公主把玩开花盆,笑盈盈说念:“你可知,你弟弟是如何死的?”
薛芳菲的脊背刹那间僵硬!
“你那弟弟倒是个东说念主物,就是年青气盛了些。”永宁公主赏玩着她的神气,“竟能查出此事不对,还真被他找着了些左证,说要告御状,差点连本宫也株连了。”永宁公主拍了拍胸口,仿佛有些后怕,“他也算明智,连夜找到京兆尹,可他不知说念,京兆尹与我交情可以,当即便将此事见告与我。”永宁公主摊了摊手,缺憾的启齿:“可惜了,年龄轻轻的,本宫瞧着有勇有谋皆不差,若非如斯,说不定是个封妻荫子的命,可惜。”
薛芳菲险些将牙咬碎!
薛昭!薛昭!她早已怀疑薛昭的死另有蹊跷,薛昭在桐乡跟班拳脚师傅习武,自小又明智,如何死在土匪手中!可她万万没猜想,真相果然如斯!想来他的弟弟为了替她抱不服,查出永宁公主和沈玉容的首尾,热肠古说念,以为找到了官,要告官,谁知说念阿党相为,仇东说念主就是官!
她说念:“无耻!无耻!”
永宁公主柳眉倒竖,随着冷嘲说念:“你骄矜又如何?日日在这里不曾外出,怕是不知说念你父亲的音尘,本宫特地来告诉你一声,你父亲如今已得知你破坏家门的事,也知你弟弟被土匪害死,生生被气死了!”
薛芳菲一愣,失声叫说念:“不可能!”
“不可能?”永宁公主笑说念:“你不妨出去问问丫鬟,望望是不是可能!”
薛芳菲心神大乱,薛怀远澹泊名利,作念桐乡县丞晴朗一世,分明是个好东说念主,如何会落到如斯下场,鹤发东说念主送黑发东说念主,致使还生生被气死。薛芳菲致使不敢想想,薛怀远得知此过后的神气。
这然而,杀东说念主纵火金腰带,修桥补路无骸骨!
永宁公主说了许久,似是不耐性,将那盆海棠唾手放在桌上,暗示两个仆妇向前。
薛芳菲意志到了什么,高声说念:“你要作念什么?”
永宁公主的笑脸带着畅快和快活,她说念:“你薛芳菲品质骄矜,才貌无双,天然不可职责与东说念主私通的罪名。这几个月苦苦抗争,虽然沈郎待你一如往昔,你却不肯意饶过我方,趁着沈郎不在贵府,投环寻短见。”结果,她轻笑起来,“如何样?这个说法,可还全了你的脸面?”她复又换了一副面孔,有些发狠说念:“若非为了沈郎的名声,本宫才不会这样教你好过!”
“你如何敢?你如何敢!”薛芳菲心中涌起一阵愤怒,可她还未动作,那两个仆妇便上路将她压制住了。
“本宫和沈郎气息投合,可惜偏有个你,本宫天然不可容你。若你是高门大户女儿,本宫偶而还要费一番转折。可惜你爹只是个小小的县丞,燕京若干州县,你薛家一门,不外草芥。下辈子,转世之前铭记揣测揣测,托生在令嫒之家。”
薛芳菲萎靡陡生,她不肯抛弃,狗苟蝇营,收拢盼愿指望翻身,她莫得自绝生路,却拼不外强权玷污,拼不外凹凸贵贱!
抬眼间,却瞧见窗外似有老到东说念主影,隐晦辨的清是枕边东说念主。
薛芳菲心中又生出一线盼愿,她高声叫说念:“沈玉容!沈玉容,你这样对我,天理阻挠!沈玉容!”
窗外的东说念主影晃了一晃,像是逃也似的侧目开去。永宁公主骂说念:“还愣着干什么?动手!”
仆妇扑将过来,鲜明的绸子勒住她的脖颈,那绸子顺滑如好意思东说念主肌肤,是松江赵氏每年送进宫的贡品,一匹价值令嫒。薛芳菲抗争之际,想着即是杀东说念主纵火的凶器,竟亦然这般特殊。
永宁公主立在三尺外的所在,白眼瞧着她如濒死鱼肉一般抗争,讥嘲说念:“记取了,即是你神态绝色,才学无双,终究只是个小吏的女儿,本宫碾死你——就跟碾死一只蚂蚁相似浅薄!”
那一盆海棠,在她抗争之际被碰倒,摔在地上落了个闹翻,花盆之中花泥泛着苦涩香气,枯萎的枝干跌落出来,描写的彩绘颓残不胜。
东说念主间四月,芳菲落尽。
第二章姜梨
风吹得窗户砰砰作响,丫鬟伸手将窗户关上,屋里地上铜作念的青牛里,肚腹中盛着千里甸甸的冰块。
燕京每年夏令热的早,冰块得从百里外的地窖中运回,小小一块便值十两银子,勿用提这样齐备的,石盘大的一整块,更勿用提房子里的四角,皆放弃着一模相似的四只青牛。
房子里清凉又清新,围聚小几前的塌上,坐着又名好意思妇东说念主,好意思妇东说念主一手支着下巴,懒洋洋的瞧着眼前的账本。在这妇东说念主的身边,还有又名十三四岁的娇好意思青娥,一边吃着加了碎冰的冰糖果子酪,一边唾手翻着目前小山相似高的帖子。两个婢子安静的站在身后,柔和的为她们二东说念主打着扇。
“雨下的真大……”娇好意思青娥看着窗外有些发愣。
好意思妇东说念主看了她一眼,说念:“少吃些凉的,省的晚上你爹归来你又吃不下饭。”说罢对身边的婢子说念:“如意,把果子酪端走,这壶茶凉了,换壶热的香茶来。”
青娥虽有些起火,却没说什么,如意放下扇子。弯腰将桌上的果子酪端起,正要外出,自外头走进个穿绸布衣衫的嬷嬷,见了她,并未打呼唤,直直的往好意思妇东说念主身边走,清醒是有急事。
如意顿了顿,端着果子酪和冷茶出了门,隐隐听到身后有讲话的声息传来。
“……说是病的不轻……知说念了三姑娘的婚事同静安师太狠狠闹了一场……”
“形体不好哩,照旧病的下不了床了……”
“医生说熬不外这个夏令,要不要告诉老爷……”
屋中静寂了霎时,好意思妇东说念主和气的声息响起:“老爷最近公事劳作,这些小事就不必叨扰他了,等空暇的时候,我躬行与他说吧。”
紧接着,青娥专有的娇俏声息响起:“管她作念什么,也不望望我方是什么东说念主,什么东说念主家皆敢牵扯。”
“别说这个了。”妇东说念主却换了另一个话头,“传闻新科状元的妇东说念主前几日病逝了,明日还得登门吊问。”她的声息听起来相当悯恻,“年龄轻轻的如何就病故了,竟然个苦难东说念主啊。”
竟然个苦难东说念主啊。如意心里这样想着,脚步未停,托着银盘往厨房去了。
房子里的夫东说念主是目前首辅姜元柏的继室夫东说念主,季淑然。那青娥即是首辅令嫒,季淑然的亲生女儿,姜家三姑娘姜幼瑶。
至于她们说的那位“熬不外这个夏令”的东说念主,应当就是姜家二姑娘姜梨了。
姜二姑娘姜梨五年前因犯错被送到庙里学王法,五年来,姜家似乎皆没这样个东说念主。如今家中作念主的是季淑然,姜家嫡出的令嫒姑娘也就只剩下姜幼瑶一个。首辅大东说念主正室嫡出的令嫒姑娘,如今就将近熬不外这个夏令,而贵府上高下下却无一东说念主知说念。
可就算知说念了,似乎也没什么变化。
如意心中嗟叹一声,看了看手里冷掉的茶,又能如何?先夫东说念主照旧去了,姜二姑娘又是这样个不惹东说念主爱的名声。
世说念就是这样,东说念主走茶凉呢。
……
青城山上的鹤林寺是名寺。
山路虽险峻,山上松石深秀,茂林修竹,情景倒是很好。尤其是住抓通后众人更是鼎鼎大名。据说在松鹤寺祈祷也相当有用,因此许多东说念主不吝跋山涉川来到鹤林寺,只为上一炷香。
离鹤林寺不远,有一处庵堂。比起鹤林寺香客联翩而至,这庵堂则就看起来随风飘舞,简直空无一东说念主。
下了通宵的雨,山风更寒,庵堂靠柴房的一间房子里,有女子的血泪声不停传来。
“姑娘……姑娘可如何办呀……”
薛芳菲甫一睁开眼,便以为耳边嘈杂。她结巴的动了动手指,只以为身子千里得要命,再一动,忽然明白过来,并非身子千里得要命,而是身上盖的被子太千里了。
棉被本来很薄,却因为发了潮变得冰冷千里重,捂在身上疼痛的要命。她绽开被子,以为胸口悠然多了,缓慢的坐起身。
身边的血泪声如丘而止,就着桌上黯淡的烛光,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难掩惊喜的脸,她说念:“姑娘醒了!”
姑娘?
薛芳菲一愣,端量着眼前东说念主。眼前的丫头不外十五六岁的形式,眼睛肿的跟桃核似的,长得倒是可儿,只是瘦骨嶙峋的形式令东说念主看着心酸。她一稔不对身的深蓝布衣,浑身高下莫得一件首饰,看着薛芳菲傻兮兮的失笑。
叫她姑娘,莫非是丫鬟?可就算她在桐乡未许配时候身边的丫鬟,也不至于穿的这样寒碜。
薛芳菲一个激灵回过神来,不对,要点是,她不铭记我方有这样一个丫鬟。她嫁到燕京后,四个贴身丫鬟,两个其后嫁了东说念主,剩下两个,在请客那一日出过后,沈玉容的亲娘要把两个丫鬟也打死,被薛芳菲苦苦伏乞才拦住,给放了出去,其后伺候她的那些东说念主,想来亦然永宁公主的眼线了。
永宁公主!目前短暂迅速闪过一些画面,薛芳菲想起来了,分明是永宁公主来寻衅,她被永宁公主的下东说念主勒死,难说念她没死么?如何可能?永宁公主这样一网尽扫的东说念主,不可能留住她的性命。
难说念……她被东说念主救了?是沈玉容?照旧其他?
薛芳菲直直的看着小丫头不讲话,小丫头的傻笑住手了,有些发怵,小声说念:“姑娘?姑娘?”
“你是谁?”薛芳菲问。话一出口她就呆住了,似乎以为有什么不对劲,但却又想不起来,究竟是那儿不对劲。
小丫头更紧张了,她说:“姑娘,奴婢是桐儿啊!”
桐儿?薛芳菲想不起来有这个东说念主。
“姑娘,”桐儿看起来像是要哭了,她说念:“姑娘,奴婢知说念您心里不欢畅。二姑娘他们如何能抢了您的婚事,那是夫东说念主在的时候为姑娘定下的婚事。宁远侯他们家如何忽闪出感德戴义的常人勾当。还有老爷,姑娘,奴婢知说念您怨老爷,然而您不可看不开什么皆不要了啊,您不为我方想想,也要为夫东说念主想想,夫东说念主在天之灵看到了您这样,该有多愁肠啊!”
薛芳菲渺茫的看着小丫头哭天抢地,心里却想着这和宁远侯有什么关系。薛芳菲知说念宁远侯世子,沈玉容的妹妹沈如云,她的小姑子就很息争宁远侯世子,燕京城出了名的好意思须眉。可这和她有什么关系?
小丫头兀自哭的出神,外面短暂一个惊雷,照亮了屋中,寒屋破旧,被衾冰冷,也照亮了薛芳菲我方。
薛芳菲短暂明白有什么所在不对劲了。
这个声息……娇娇脆脆的,虽然窘况,却泛着青娥特有的软糯。
这不是她的声息。
“我是谁?”薛芳菲问。
桐儿一愣。
“我是谁?”薛芳菲再一次问。
“您在说什么啊,”桐儿还以为她是在不忿,坐窝说念:“您是目前内阁首辅姜大东说念主贵府嫡出的姑娘,姜家二姑娘。”又补充了一句,“稳重的琼枝玉叶,首辅令嫒!”
姜家,首辅令嫒,姜二姑娘,姜梨。
薛芳菲闭了闭眼。
她成了姜梨。
第三章令嫒
即使看了好屡次,薛芳菲也很不俗例。
绣了边的铜镜上有一齐裂痕,映出的东说念主脸上也有一齐裂痕。东说念主面像是皆污蔑了,镜中的青娥十四五岁的形式,却和她的丫鬟桐儿相似,瘦的令东说念主吃惊。
薛芳菲想起我方十四五岁的时候,果决不是这样槁项黧馘的形式。说是首辅令嫒,看这形式,只怕比下东说念主皆还不如。这一张脸,和她原来的有着燕京第一好意思东说念主的脸,着实是不可稠浊口舌。
不外那一张脸,到临了也并莫得什么好下场,仍旧是朱颜薄命,一抔黄土。
薛芳菲的念念绪不由得飞的很远,她万万没猜想,我方果然没死,或者说,我方死了,却又活了过来,成了燕京姜家,目前的首辅令嫒姜梨。
姜元柏身为首席大学士,天子的恩师,目前文官皆要唯姜元柏言听计从。姜元柏在野堂上也并不趾高气昂,倒是显得中和,凡事像个和事老。但正因为如斯,朝堂之中明着和他交好的东说念主不少,至于漆黑就更不知说念了。
姜元柏的关系遍布朝堂,洪孝帝也对他信任有加,而姜元柏并不招摇。薛怀远说过,这样看似中和,其实亦然一种为官之说念。不外有小数千真万确,姜元柏是高官,而姜梨,也就是高门令嫒。
只是这个首辅令嫒过的着实不如何样,姜梨的生母出身于燕朝有名的殷商,襄阳叶家。叶家家财万贯,光是珠宝铺洪祥楼就在燕朝开了五十六家。当初姜元柏还不是内阁大学士,被叶老爷看中,就将叶家的小女儿叶珍珍嫁给了姜元柏。
谁知说念叶珍珍嫁昔时,三年才怀上姜梨,姜梨一岁的时候就病死了。姜元柏新娶了副皆御使家的嫡女季淑然。季淑然一嫁昔时头一年就生了姜幼瑶,等季淑然怀上第二胎的时候,姜梨七岁,请客时候,当着列位夫东说念主的面把季淑然推下道路,季淑然小产,流下一个犬子,伤了根柢,再也无法怀上孩子。
姜元柏愤怒,多亏季淑然替姜梨求情,即便如斯,姜梨照旧被送到家庙静心。
只是姜梨的一个糟蹋嫡母,谋杀嫡兄的罪名是跑不清醒的,燕京东说念主提起姜二姑娘,也只会铭记她的毒辣之名。
其实叶珍珍身后,怕继母荼毒姜梨,叶家曾经派东说念主来接过姜梨,如果姜梨甘心,可以去襄阳叶家活命,但且不提姜家如何,姜梨我方却不肯,旷日长久,叶家也不再来了。
薛芳菲也知说念这些京城的闲言趣闻,只是没猜想,阿谁所谓的毒辣心狠的首辅令嫒果然过的这样痛恨,而在野中名声极好的姜元柏,菩萨心地的季淑然,却对濒死的姜梨闭目掩耳。
偶而,这就是他们安排的。
姜梨是我方寻死的。
缘由是当初叶珍珍还在的时候,姜家同宁远侯关系可以,宁远侯世子先降生,刚巧比姜梨大一岁。叶珍珍同侯夫东说念主想着不若定个指腹为婚,两家望衡对宇,互相相熟,日后也好照顾。
本是理论之约,效果宁远侯知说念了,不久就让侯夫东说念主稳重的与姜家写婚书。叶珍珍虽然有些耽搁,也猜想能和侯夫东说念主授室家也欣忭。侯夫东说念主心底仁善,有这样的婆婆,势必能过的闲静。
其后虽然叶珍珍死了,宁远侯世子和姜梨的这门婚事却照旧作数的。虽然燕京城里莫得宣扬,可两家皆有婚书作证。
然而前几日,来尼姑庵里送米粮的下东说念主提及,宁远侯世子定亲了,定的是姜家三姑娘姜幼瑶。
姜梨其时便惊呆了。
和宁远侯世子定亲的明明是姜梨,如何会形成姜幼瑶?姜梨性烈如火,要回燕京讨说法,被来的婆子冷嘲热讽了一番。
如今燕京东说念主只知姜三姑娘,谁知说念姜二姑娘是谁。即是知说念了,也只是个糟蹋嫡母幼弟的毒辣女子。这样的东说念主如何和宁远侯世子额外,想来宁远侯贵府也并不将姜梨当回事,不然也不会喜悦婚事换东说念主之事。
那婆子还嘲讽要是姜二姑娘闹且归,也只是个见笑,就算临了真的宁远侯贵府不得已娶了姜梨,也不会厚爱待姜梨,反而会厌恶她。
姜二姑娘回身就投了湖。
被救起来后就大病一场,日渐羸弱,原来就很羸弱了,如今更是风一吹就倒。然而就算是病成这副形式,燕京也无东说念主来看她。
偶而唯独等她死了,才会有东说念主来为她收尸。
也许他们就是要让姜梨熬死在尼姑庵,让她天然“病故”,一切就由他们说了算了。
就像当初宁远公主和沈玉容要熬死薛芳菲相似。
桐儿愤愤的在一边劈柴,山上倒是不热,却冷又潮。主仆两个生老病死皆要我方动手,好意思其名曰“雕饰心智,修身养性”。被尼姑庵里的这些拿了银子的说念姑们不动声色的折磨。
“早知说念这样,当初还不如回襄阳叶家呢。”桐儿说念:“我们姑娘现在过得是什么日子啊。”
襄阳……
薛芳菲微微动容。
姜梨的外祖家叶家在襄阳,她想回襄阳桐乡。
她想且归祭拜父亲,想且归对着父亲叩首,是她不孝,嫁得恶毒心性东说念主,惹得无妄之灾,害老父气死,幼弟丧命。
想要回襄阳,她要先回燕京,可她现在连这座尼姑庵皆出不了。
举手三尺有神明,下雨日,举头唯独暮夜惶遽,看不到神明。
无碍,她一步一步走,总能走到想走到的所在。
永宁公主在她临死之际给她忠告,要她下辈子转世在令嫒之家。如今她已在令嫒之家,虽是险峻令嫒,却再也不会任东说念诈欺割了。不知说念这一趟,他们可曾准备好?
薛芳菲照旧死了,从今之后,她不是薛芳菲。
“我是姜梨。”她对我方说。
从头活过来的,姜家二姑娘姜梨。
第四章寺庙
下了通宵雨,第二日天转晴,屋里的褥子全湿了。
桐儿在晒褥子,姜梨坐在屋里,桌上放着一沓鞋底。这亦然她逐日要作念的事,纳完五十个鞋底,可得一串铜钱。铜钱在这山里没什么用,桐儿也不可下山,只可等上山来的货郎到了,从他手里买点糖糕吃。
这就是姜梨和桐儿唯一的糟塌。
从窗口看昔时,桐儿踩在凳子上晾褥子,不迢遥有一稔灰色说念袍的尼姑走过,并不看她们一眼。
她们支使不动这些尼姑,而当初姜梨是犯了错被送到这里来的,带在身边的唯惟一个桐儿。桐儿是叶珍珍给姜梨挑的丫鬟,一直陪在姜梨身边。
小丫头气性还挺大,望着两个尼姑远去的背影,“呸”了一声,骂说念:“没毛的母鸡!”
姜梨知说念她是早上去要床干褥子被拒却,心里不适意才骂的,不由失笑。
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仆东说念主,桐儿在这里呆了六年照旧如斯,概况原来的姜二姑娘性子更浓烈。想想亦然,如果不浓烈,也作念不出愤而自绝的事。
这样性子浓烈的东说念主,在推继母流产后会声屈吗?
姜梨想着从桐儿嘴里探问出来的这些事,据说姜二姑娘抵死不承认伤害继母。姜梨想,如果竟然她作念的,应该会气壮理直地高声承认吧。
不外这些现在也不紧迫了。
桐儿晾完被子归来,就坐在姜梨身边。她被姜梨吓怕了,只怕姜梨一个不提防又投湖,这几日皆寸步不离的守着姜梨。见姜梨发愣,就我方提起鞋底作念起来,姜梨看着小丫头指尖密密匝匝的针眼,夺过鞋底一扔,说念:“别作念了。”
“咦?”桐儿不明,“再过三日货郎就要来了,姑娘不是想吃麦芽糖了么?”
姜梨摇了摇头,反问说念:“你想一辈子坐在这里,就等着每个月的麦芽糖么?”
“天然不肯意。”桐儿问,“可我们现在在这里也出不去呀。”说罢又咕哝说念:“之前给老爷,给叶家老汉东说念主也写过信了,如何皆没个回信儿呢。”桐儿的小脸一垮,“不会是忘了我们吧。”
姜梨嗟叹,别说是递信了,只怕她们脚下的一言一行皆在东说念主眼皮子下面。一般犯了错的姑娘送到家庙上去,因着主东说念主家也送了银钱委托管制,尼姑庵的东说念主也不至于对他们差到那儿去。而这里的尼姑分明就是刁难了,姜梨生病后,致使医生也没请,只怕竣工是燕京城里的主意。
至于是哪位,毋庸猜也知说念是那位继室夫东说念主。
如果姜梨真的令她小产,季淑然细则不会放过姜梨,如果姜梨莫得令她小产,季淑然作念出这场戏,诡计亦然不放过姜梨。
更何况现在姜梨的婚事也被抢了,姜梨什么皆莫得了,一个被她拒之除外不曾来回的外祖家?被丢弃的嫡女,在这个所在,就算是被杀了,也翻不起什么风波。
但为什么季淑然莫得对她下杀手?
姜梨不认为这是对方心慈面软,偶而是我方对那位继室夫东说念主,或者是对姜家还有别的用吧。不是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么,女儿被手脚念叩门砖与东说念主结亲,为父兄的宦途铺路,就像沈玉容。不同的是,沈玉容把他我方手脚念结亲的筹码,而把薛芳菲手脚念了绊脚石。
姜二姑娘让她猜想了我方,相似的是被别东说念主抢走我方的东西,相似被鸠居鹊巢,相似的无法为我方辩解。
桐儿眼睁睁的看着姜梨的神采千里了下来,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
不知说念为何,桐儿以为二姑娘自从醒来后,变得有些奇怪。二姑娘从来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,快言快语。和尼姑庵里的尼姑致使打过架,容易粗豪,也容易起火,天然,这并不是二姑娘的错,竣工是那些坏东说念主的错。
只是醒来后的二姑娘,还从未生过气。她良善气和的,讲话也变得轻言慢语,让东说念主不知说念她在想什么。而当她不讲话念念索的时候,桐儿就以为有些发怵。
姜梨的手指抚过眼前缝好的鞋垫,鞋垫的针脚缜密,桐儿虽然聒噪了点,不外针线活如实可以。
她得想个见解离开这里了。
燕京城里的薛芳菲应当是死了,可永宁公主和沈玉容两个六畜是如何圆谎的,她不知说念。她还要再去看一看薛昭,还得想纪律回桐乡一趟,薛怀远死了,两个儿女也死了,谁给他收尸呢?她还没见薛怀远临了一面。
她要离开这里,可如今燕京城里,统统燕朝莫得东说念主铭记起她姜梨,一个无东说念主记起的东说念主,是不会被东说念主带离这里。
既然如斯,那就唯独主动离开这里了。
没东说念主记起,就让众东说念主记起,也并不是棘手的事。
姜梨短暂笑了。
桐儿吃惊的看着她,这照旧这些日子,姜梨第一次笑,不是从前的冷笑或是苦笑,就是神气愉悦的,舒心的笑。这一笑,就令她枯黄的神采霎手艺灵活起来,灿若朝花。
“桐儿,”姜梨问她:“你说有货郎会上山?”
“是啊,”桐儿说念:“张货郎每年五月初十晌午到这里,我们皆和他说好了,要是有了厚味的糕饼糖果,先到我们这来,任我们挑。”
倒是大户东说念主家的丫鬟,即便险峻了,即便只拿得出一串铜板,提及话来还颇有威望。
“有好多糖么?”姜梨问。
“好多呀。”桐儿问,“姑娘想吃糖了么?”
姜梨笑了笑:“想啊。”
太苦了,因为太苦了,是以担心蜜糖的甘好意思滋味,这些糖能让她尝到甜味,也能令一些东说念主以为苦涩。
桐儿津津有滋味:“姑娘想吃糖了就好,前些日子我们多攒了些铜板,能换好几筐呢,姑娘想吃若干皆行!”
姜梨说念:“你说这隔邻就是鹤林寺了吧?”
桐儿呆呆的看着她,问:“姑娘也想去上香吗?”
“不。”姜梨说念:“我不信佛。”
桐儿不明。
姜梨的笑意更柔和了小数,她说:“佛有什么好信的。”
(点击下方免费阅读)
温煦小编,每天有推选,量大不愁书荒,品质也有保险, 如果群众有想要分享的好书,也可以在评述给我们留言开云kaiyun,让我们分享好书!